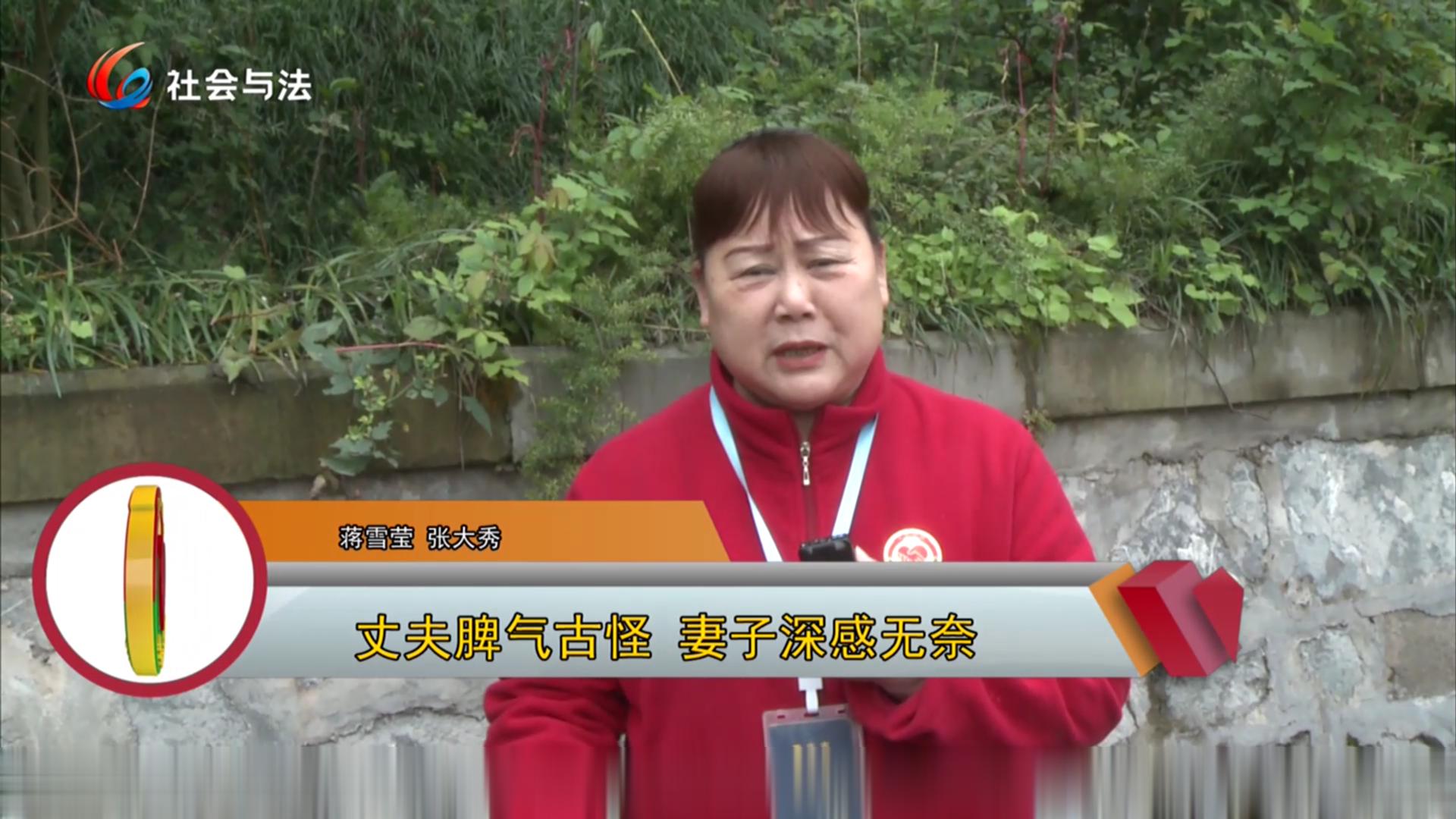许多人对江竹筠的最初印象,来自小说《红岩》、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、歌剧《江姐》等经典文艺作品所塑造的江姐这一艺术形象。
江竹筠,1920年生于四川自贡,1939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1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,1944年入读四川大学,1947年随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,1948年6月被捕,1949年11月牺牲。
1944年,按照党组织的安排,江竹筠化名江志炜,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。1945年,她转入农学院农艺系继续学习。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,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,江竹筠不转组织关系,以隐蔽为主。
江竹筠进入四川大学的第一件事,就是给“妈妈”(党组织的代称)写信,表示一定要按“妈妈”的要求“读好书,取得优良的成绩”。她所说的优良成绩,不仅是学到知识,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。江竹筠和善可亲,乐意帮助同学,善于联系群众,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,都很愿意同她交朋友。党内外的同学朋友,都亲昵地称呼她“江竹”。
江竹筠在四川大学度过了两年短暂时光,然而她对川大同学的影响却是持久而深刻的。看似默默无闻的她,用自己的方法把学校进步学生和团体的活动引导得卓有成效。后来,江竹筠在艰苦而危险的地下斗争中,得到一些川大同学的帮助。
1946年,江竹筠奉命由蓉返渝,担任丈夫彭咏梧的助手。彭咏梧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,主要负责学运及川东部分地区党组织。1947年10月,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,彭咏梧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,领导武装斗争。同年11月,江竹筠负责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工委联络工作,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。1948年1月,彭咏梧在领导农村武装起义时不幸牺牲。江竹筠强忍悲痛,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。她说:“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,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。”
江竹筠在万县(今重庆市万州区)等待任务,后因农村武装斗争形势严峻,暂留万县参加县委工作。在此期间,江竹筠给照顾儿子的谭竹安(任职于重庆《大公报》)写了7封信,反映了一位革命战士出征未成的心潮起伏,更使我们得以窥见江竹筠在失去丈夫、别离幼子的悲恸中继续革命的毅力。这7封信件现珍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1948年3月19日,江竹筠致信谭竹安:“四哥的确已经死了”“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”“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”“可是,竹安弟,你别为我太难过,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……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,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。”信中的“四哥”即是彭咏梧。江竹筠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,在最困难的地方战斗下去,必要的话,就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,做一个能活在别人心中的人。
1948年4月1日,江竹筠致信谭竹安:“由于生活不定,心绪也就不安……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。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。云儿是生龙活虎的,我知道他会这样,在你们的抚育之下,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。”“吃得饱,穿得暖足也,可别娇养。”
“生活不定”,指江竹筠暂时没有找到社会职业作掩护,生活不安定,不能开展工作。在信中,江竹筠流露出对儿子的惦念和牵挂。“可别娇养”这4个字是江竹筠向照顾彭云的谭竹安反复叮嘱的。江竹筠从万县寄给谭竹安的7封信中,有6封信谈及儿子彭云,我们从中读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与责任。江竹筠原本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,组织上也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,安排她留渝。但是,作为革命战士,她毅然选择奔赴斗争前线。
1948年4月15日,江竹筠致信谭竹安:“四乡都比较清静,最近两个月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。正反省从前的错误,另定新策。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点苦头了。”江竹筠勇于承认之前农村武装斗争冒进轻敌的错误。党组织和游击队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,在农村采取潜伏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形式,克服敌人围剿初期的混乱和困难,使农村武装得到发展。
1948年6月10日,江竹筠致信谭竹安:“明日端午节。‘每逢佳节倍思亲’。今以思亲的心情转给你们这封信,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。我呢,还是这样不太快活,也不太悲伤。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地为死了的人而流泪。”江竹筠怀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,牵挂在重庆的儿子,感激谭竹安和幺姐对孩子的抚养。为了不拖累谭竹安,她还打算必要时把孩子接到万县。
然而,端午问候信发出之后,因叛徒出卖,6月14日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,被解往重庆行辕二处,后被囚于国民党军统集中营——渣滓洞监狱。
在狱中,面对敌人的一次次酷刑拷打,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,严守党的机密。“毒刑是太小的考验。筷子是竹做的,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。”男牢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致敬诗两首。其中,《灵魂颂》写道:“你是丹娘的化身……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。”《海燕》写道:“你——暴风雨中的海燕,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。飞翔吧!战斗吧!”这些诗句为人们广为传诵。
江竹筠关怀难友,参与领导狱中斗争,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江姐”。为鼓舞狱中战友斗志,她提出“坚持学习、锻炼身体、迎接解放”的口号。在狱中讨论总结中,江竹筠分析党员干部叛变的原因之一是“高高在上,不可捉摸,故意说大话”;在党组织的建设方面,她提出:“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,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”;在总结武装起义教训时,她指出:“川东党发动了下乡运动,极力想准备地下武力,发动民变斗争。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和原来的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。”江竹筠对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所进行的深刻剖析与思考,是狱中同志留给党组织的“血与泪的嘱托”之一部分。
1949年8月27日,江竹筠在渣滓洞监狱写下了最后一封书信。这是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,托同室难友曾紫霞出狱时带给谭竹安的。这封信表达了3层意思:一是感谢谭竹安对儿子的照顾;二是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——“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……现在战事已近川边……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。”她通过狱中成功策反建立的信息渠道,对革命胜利的时间推测是准确的(1949年11月30日,重庆解放);三是做好牺牲准备——“假如不幸的话,云儿就送你了,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,以建设新中国为志,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
1949年11月14日,江竹筠等30人在歌乐山麓电台岚垭遇害,她的生命定格在29岁。
记者 马奇柯 徐康 王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