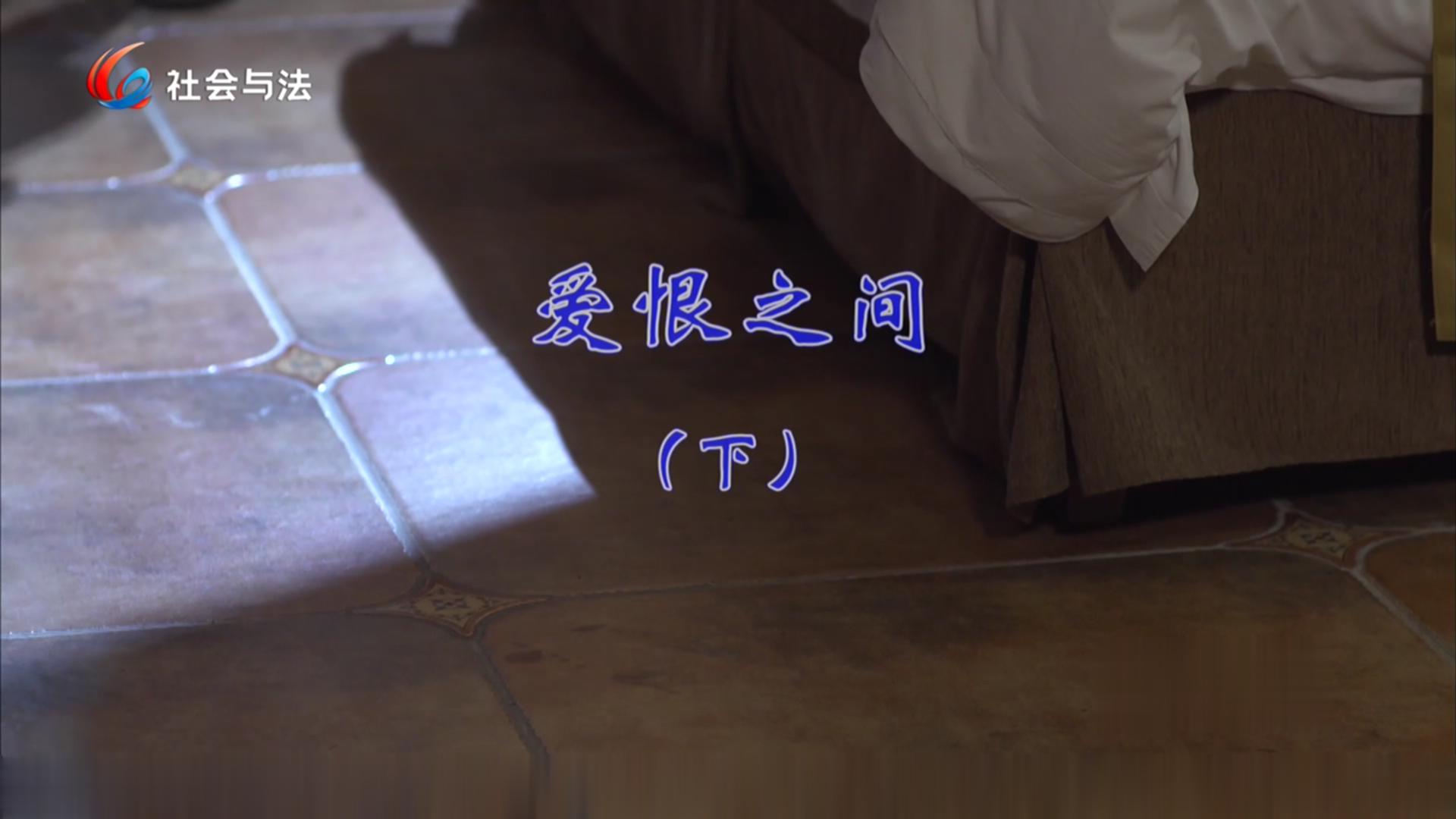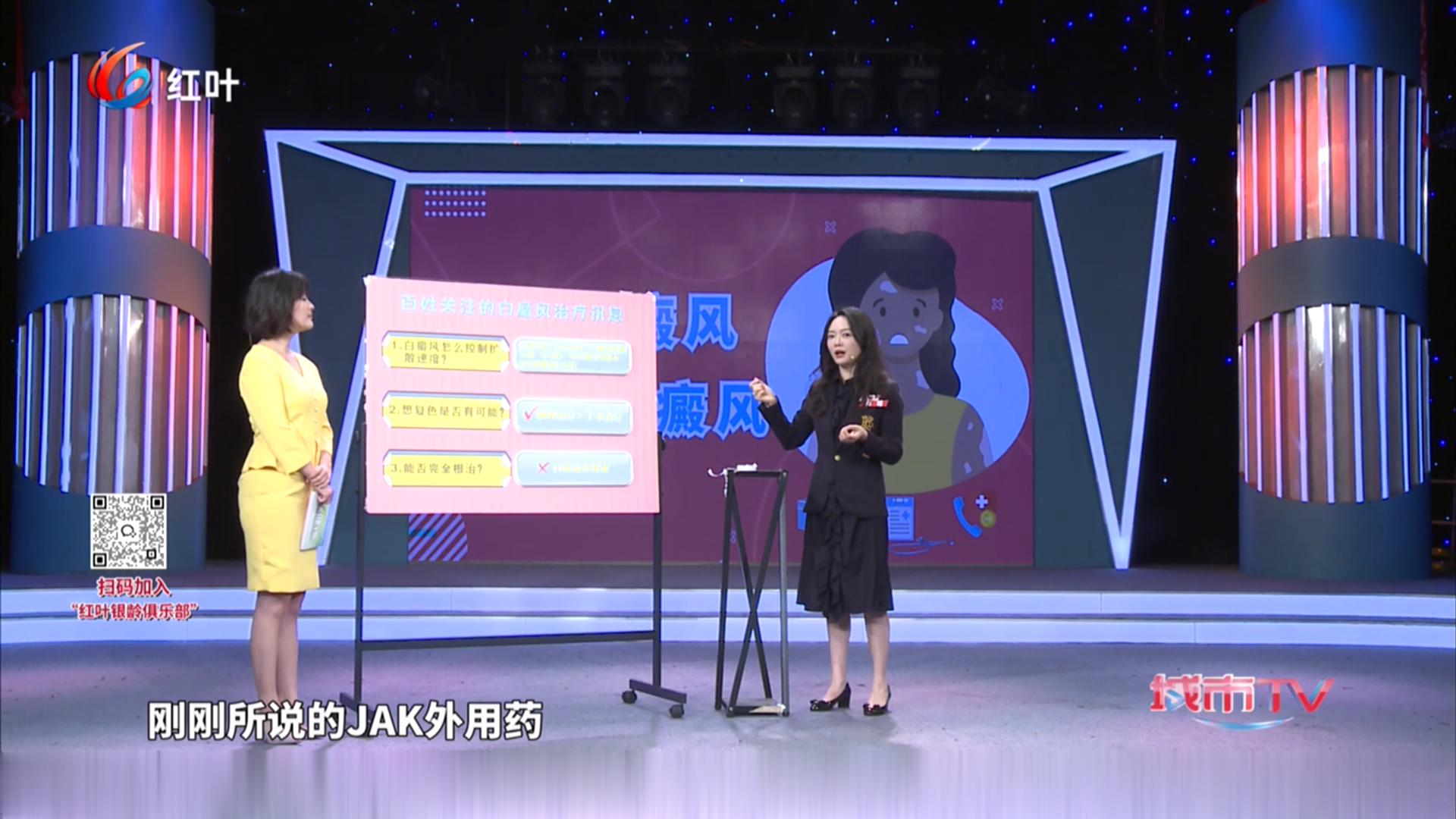“啦啦啦,啦啦啦,我是卖报的小行家,不等天明去等派报,一面走,一面叫,今天的新闻真正好,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……”这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《报童》的主题曲。今天,当我们重温这首歌曲时,眼前仍能浮现出报童们脚穿草鞋,身挎布袋,满身泥泞,手中挥舞着《新华日报》沿街叫卖的情形。当年在重庆,就是这些被誉为“新华小尖兵”的报童,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,将党的声音送进了国统区的千家万户。他们绝大多数还是青少年,却对党无限忠诚;他们虽遭受关押毒打,却甘愿奉献一切。这是怎样一种情怀,怎样一种精神?
新华日报社最初没有自己的报童队伍。1939年,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,对《新华日报》采取“只准印,不准卖”的扼杀政策,没有人敢卖《新华日报》。于是,报社便开始培养一些胆大的流浪儿童建立自己的报童队伍,最多时达到130余人。
1941年1月,皖南事变爆发,为揭露事实真相,报童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周旋,将印有周恩来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,同室操戈,相煎何急”题词的《新华日报》送到读者手中。面对特务的抓捕、毒打,报童越战越勇,到街上散发报纸。这是电影《报童》的高潮,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。
据统计,1941年2月4日至16日的13天中,有11名报童被关押殴打达35次。2月4日这一天,国民党宪兵在重庆两路口逮捕了4名报童,扣押了几捆《新华日报》。报社同志多次交涉无效,直到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抗议,4名报童才得以释放。
据《新华日报》发行科主任罗戈东回忆,“皖南事变后,发生过多次报童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、毒打的事件。黄光武、石永祥、李云甫等报童被打伤,甚至口吐鲜血,伤势未愈又开始卖报。我为他们请医敷药,也被他们那种勇敢坚强的精神所感动。我很高兴他们在斗争中逐渐成长”。《新华日报》日发行量从国民党封锁时的200余份,逐步上升至5万份之多,而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日发行量仅1万余份,两个数字的对比,充说明报童们的无畏付出和辛勤劳动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“编得好、出得早、销得多”是新华日报社全体同仁奋斗口号。所以,无论酷暑还是严冬,报童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,天不亮就背着重达20斤左右的报纸,往返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去送报卖报,但是他们从不叫苦叫累,即便去最危险的地方也从不退缩。
1943年春,原本负责南岸汪山、黄山路线的报童被特务抓去,读者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报纸。罗戈东和营业部主任孙达成经过仔细考虑,选中了胆大心细的报童蒋维芳,并与他进行谈话。罗戈东介绍情况说:“汪山、黄山一带是蒋介石居住的地方,国民党防范很严,《新华日报》的发行难度很大。但是,山上有很多学校,我们要让《新华日报》去占领各个学校,让那里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前方打日本鬼子的胜利消息!这一带是最困难的地方,小蒋,你敢去吗?”蒋维芳不犹豫地回答道:“敢去!”
然而,因为没有去过这条路线,又没有熟悉的同志带路,订户和地址都不熟悉,而且订户的票签不能带在身上,怕被特务发现危及订户,要把100份报纸一份不落地送到订户手中,困难可想而知。蒋维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,把100多个订户的姓名、地址,牢牢记在心里。第三天,当蒋维芳把《新华日报》送到订户手中时,他们既高兴又担心他的安危,关心地问:“这几天你们先后被抓了两个报童,最近那个送报的小鬼被打得很惨,还被送进防空洞!你还这么小,难道不怕吗?”蒋维芳微笑着回答:“国民党政府准许《新华日报》出版,我送报光明正大的嘛!”几个月后,当地订户从100多人发展到了300多人。
报童们每天还要应对特务的盘查,他们大都会机智勇敢地应对,然而并非每次都能顺利躲过。1945年11月29日,蒋维芳遭便衣特务毒打,被抛进土沟内,后来被两位好心的读者发现,雇轿子抬回了报社。
对于报童,国民党特务是威逼利诱,软硬兼施。报童戴宗奎曾先后被抓过三次,遭到毒打、威胁却毫不屈服。特务第四次把小戴抓去,不打也不骂,还倒茶送糖,皮笑肉不笑地说道:“小兄弟,你喜欢卖报,就卖《中央日报》吧,到我们这边来,怎么样?”小戴“呸”的一声将唾沫吐到特务头上。特务毫不生气,继续劝道:“你要么去念书,要么去做个小买卖,不好吗?”小戴蔑视地看着他们不予回答。威逼利诱不成,特务们拿着枪到其家中,逼其母亲把儿子从新华日报社要回来,扬言道:“如果不叫你儿子离开共产党的报馆,小心你和你儿子的脑袋!”小戴是家中独子,看着儿子浑身伤痕,母亲心如刀绞,含泪劝说:“儿呀,回来吧!我就只有你这根独苗苗,特务狠心害你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你让我怎么办呀?”小戴耐心地向妈妈讲述《新华日报》发行的重要意义,最终说服了妈妈。老人不但不再阻止儿子送报,反而为有这样一个勇于为革命献身的儿子而感到骄傲。
小尖兵们立场如此坚定,觉悟这么高,与南方局和报社同志的关怀教育是分不开的。上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,下至发行科的大哥大姐,都尽一切力量关心这些小战士的成长。报童们大多出身贫寒,文化水平较低,有的最初几乎不识字。发行科的大哥大姐定时给报童们上课,并组织大家自学。在反动派封锁迫害严重时,每天晚上都组织大家交流斗争经验,研究策略。编辑部、经理部的同志还经常给大家作报告,并与他们交流。
在报社这所学校,这些青少年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得到迅速提高。他们不再仅仅为个人温饱而挣扎,而是把个人命运和革命前途联系在一起,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,很多报童最后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他们之间相互关心,相互帮助,情同手足,生死与共。
【节选自《重庆红色故事》(第二辑)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