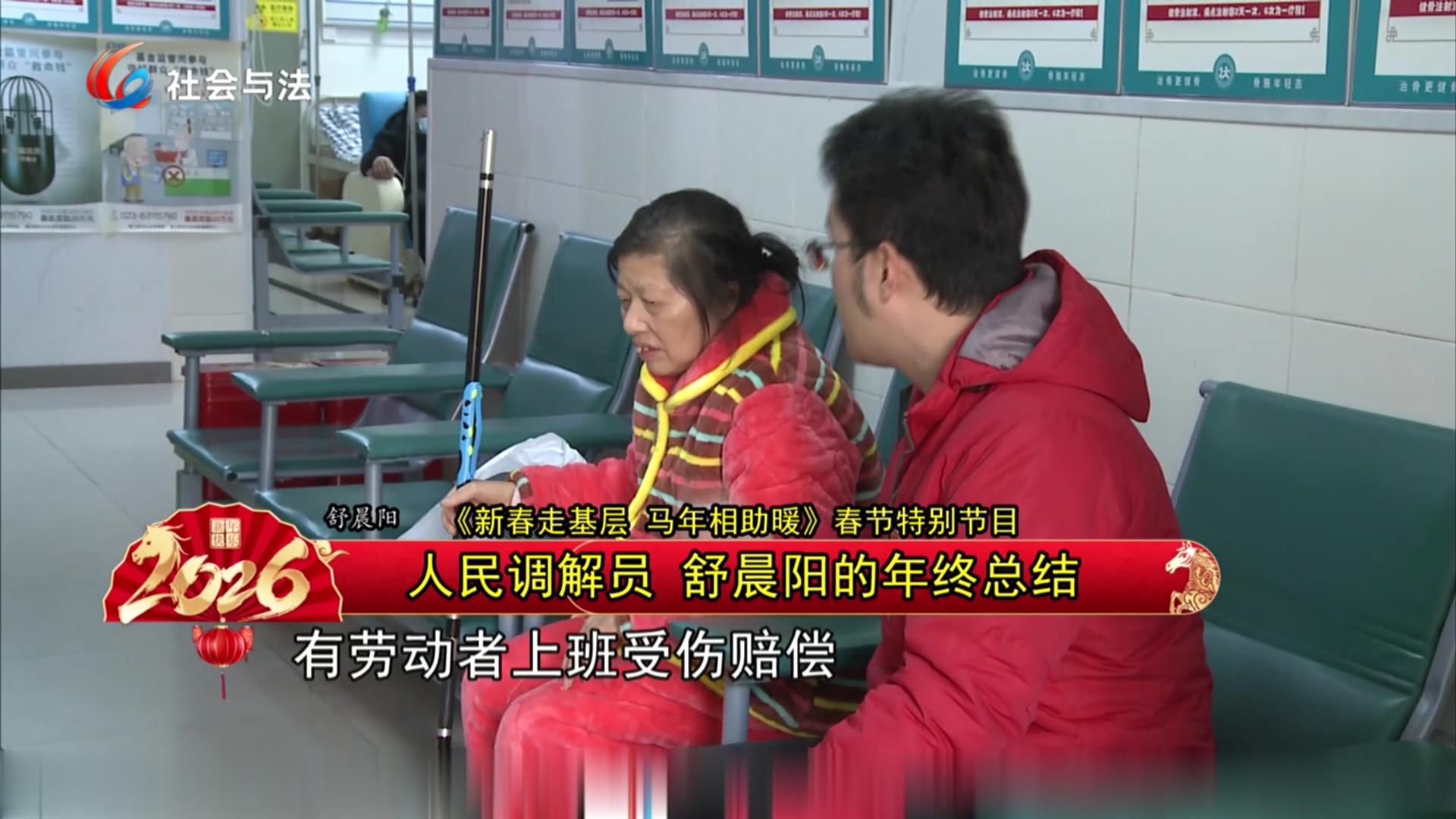沙变土
听上去似乎像水变油一样荒谬
可这并不是一场闹剧
而是重庆交通大学沙漠土壤化团队
潜心研究十几年的成果
他们成功完成沙漠生态恢复建设一万亩
使沙漠变成了绿洲
长出了庄稼

乌兰布和沙漠基地。受访者供图
我国的沙化土地有173万平方公里,如果仅改造其中1%,就可新增2600万亩可利用土地。在人均耕地少,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背景下,广阔的沙漠似乎成了亟待开垦的“耕地储备资源”。
但先别急着乐观,沙漠是否可以无限制开发?保护自然景观跟遏制荒漠化又该如何平衡?就像每一个伴随着质疑前进的重大发现,沙漠土壤化技术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但这支团队从不害怕挑战,他们从荒漠边缘到腹地深处一点点探进,在黄沙与绿意之间,探寻着人类与自然永恒的平衡。
沙与土的力学之桥
就像传说中牛顿从掉落的苹果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,团队负责人、力学教授易志坚是在研究一种新型聚合物水泥混凝土路面时,发现颗粒物质加了粘结材料后,会出现流变状态。于是在2008年,提出了沙变土的设想。
“主要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,意识到固体也是颗粒物质的一种,它成为固态只是因为颗粒被约束住了。从而可以推论出,颗粒物质可以变成固体或者液体。”易志坚说,“当时我意识到这一点后,激动得把手使劲儿一拍,结果手麻了好几天。”
他一直说,土壤其实天然具有两个生态力学属性,一是自修复,二是自调节。所谓自修复,就是固体状态下的土壤会裂开,通过吸收足够的水分,变成流变状态,把裂纹修复得无影无踪,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界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原因。而自调节属性,说明土壤能够自己调节颗粒排列,可以通过颗粒排列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体积、形状,但土壤的性质却不会随之变化。这样一来,土壤的颗粒物质之间可以存储水分、养分、空气并滋生微生物,从而让植物根系扎进去,这是保证植物在土壤中生长的关键。

乌兰布和沙漠基地里长出的萝卜。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摄
当时的易志坚面临两种选择,一是沿着原来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,当时他在做的新型聚合物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影响力很大,水泥摔不坏、砸不坏,已经在全国开始推广。如果是去做沙变土,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路。“但当时就觉得这个如果做成了,意义特别重大,所以还是选择了去走这条新路。”
“那时候就不担心设想没法变成现实吗?”
“搞力学的相信原理。只要原理对了,环境不同只是参数不同而已,怎么可能会失败?”
选择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,不仅意味着从头开始,也意味着要经历更多的困难。从提出设想到技术实现关键突破,又过了五年时间。
在进一步的研究中,易志坚团队发现,土壤颗粒间存在一种约束关系,约束下的土壤颗粒体,既有一定的柔性,能够保水、保肥和透气,为植物根系生长提供弹性空间,又有一定的刚性,使之能够“抱住”植物根系,维持植物稳定。“当时我就联想到,土壤和沙子之间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这种约束关系。”
在这个理论基础上,易志坚想到可以通过颗粒物质的约束,实现沙子到土的转变。具体方法则是在沙子中加入一种约束材料,使沙漠具有土壤的力学状态,干的时候是固体(干土团),湿的时候则为流变体(稀泥巴),两种状态之间可以自由转换。“所以这项技术并不是真的让沙漠变成土壤,而是让沙子成为植物的载体。加了约束材料后的沙子之间,产生了结合力,能够存住水分、养分和空气,作物能够生长。”
2013年,团队研发出一种植物纤维素黏合剂,上述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。“这种调理剂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后,并进行了力学上的改性,是一种环保无污染的材料,不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危害,甚至是可以食用的。用了这种材料长出来的东西,也都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。”易志坚说。
从实验室到沙漠
当技术在实验室里变得成熟,团队不想只是拿课题,发论文,甚至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论文发表,因为他们的目光不只局限在实验室的方寸之间,而是看向了我国无边无垠的广阔沙漠。“只有真的把沙漠改造成功,这项技术才算有了生命。”
团队还发现,这项技术对沙子没有特殊要求,比如沙漠里沙子有粗有细,我们做的试验显示,沙变土基本都没有问题。”易志坚表示,团队甚至用河流中的沙子进行过试验,同样可以变成土壤。
既然这样,那么所有的沙漠都可以施展拳脚,那既然要推广,就从最艰难的地方开始吧。“最难啃的骨头都能啃下来,其他的就都不是事儿了。”于是,他们把目光瞄向了1500公里外的乌兰布和沙漠。
“乌兰布和”,在蒙语里是“红色公牛”的意思,表达了这片沙漠极强的流动性。这里在西汉年间还是沃野千里,唐宋时期明显沙化,“沙深三尺、马不能行”,而今已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流动沙漠。乌兰布和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,东近流经此处的黄河,西至一处名为察汗布鲁克的盐池。这片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是挨着水的,而它的恼人之处也正是在此。

易志坚在乌兰布和沙漠基地察看向日葵的长势。受访者供图
在过去,乌兰布和沙漠是黄河冲积平原上的一片草原。而现在,它每年要向黄河流域直接输入一亿吨泥沙,是单位长度内使黄河水含沙量增幅最大的地区之一。并且,它还在扩张中,每年平均东侵8.7米,向黄河输入的泥沙也在逐年增加。
团队副研究员李亚记得,“刚来的时候,满眼一点绿色都看不到,也没有路,都是些泥巴渣土路,水、电、网络等生活设施更是一个都没有。”特别是一群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初来乍到,适应气候就是个大问题,鼻子干得天天流鼻血,只要一出门,眼睛、鼻子、耳朵里就都灌满了沙子。“漫天的风沙刮得到处都是,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。如果刮一晚上风,我们住的房屋门口就能垒起一座一米高的沙丘。”
但这群人硬是在这里扎了下来,改造起了沙漠。但让沙漠具有土壤属性只是第一步,让沙漠上长出庄稼才是最重要的。但即便是当地和沙漠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,也不相信易志坚他们能把作物种活。“我从1985年开始就在治沙站干,沙漠里面种上树之后,树根本不长,必须得年年施有机肥,灌黄河水,弄个十年八年的,树才能活。””乌兰布和沙漠基地工人张国民说。
大自然更不会因为他们是初学者就善待他们。顶着重重压力,一帮力学背景的人来搞农业生产,一开始也是闹出了不少乌龙。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播种,一颗芽没发,大家都傻眼了。他们将沙子和约束材料搅拌好,再用手推车运到基地铺满,然后忙着播种,每个人都晒爆了皮,嘴唇也裂出了血——辛苦倒不怕,可就是想不通,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
幸亏有当地的农民点拨:你们播种的季节不对!边疆春迟,播种播得太早了。团队熬到5月中旬,再次播种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葵花、小米、苜蓿……结果奇迹发生了,种啥长啥。为了摸索出哪种植物能在沙漠中更好地存活,他们一口气种了70多种植物。刚种上的苗,沙尘暴一来就全给刮倒了,只能赶紧补种。但慢慢地他们发现,作物远比想象的更有韧性。春去秋来,夏耘冬藏,点点新绿,就逐渐覆盖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黄沙。人们的生活和心情,也伴着这些改变逐渐好转起来。第二年,种植面积就扩大到4000亩,拖拉机带着旋耕机,搅拌播种同步完成,效率从每人每天几分地提高到了一天50亩。
走出实验室的第一步成功了,但这支团队还要走向更广阔的沙漠,进行大范围的产业化推广,让这项技术在更多的场景落地。“主要就是提供技术服务,比如服务有沙漠治理需求的企业和政府。”李亚举了几个例子,一些光伏企业,要在光伏板下做绿化。然后团队就开始进行沙漠改造和种植管理。或者是某地草原退化成沙漠后,当地政府让团队去恢复生态。
“改造完沙漠不就行了吗?为什么还要进行种植管理?”
“因为需求方判断沙漠是否改造成功的标准,就是看地上长出的植物好不好。”
“那沙漠是否可以无限制开发呢?”
“我们的目标就不是‘消灭’我国所有的原生沙漠,毕竟沙漠也是一种资源,也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。我们的目标是遏制荒漠化,比如恢复被沙漠覆盖的土地资源,让人们可以重新利用起来。”
绿洲为证
在乌兰布和沙漠基地里,最让易志坚自豪的是一片布满荒草的改善田地。这片地距离试验田的入口有两公里,布满了质感粗粝的耐旱植被。试验田经常有很多人来观光学习,但没人对这片荒草地感兴趣。更多的人会被基地里连片金黄的向日葵花吸引目光,会对沙地萝卜的清香口感赞不绝口,或者对脚下青绿色的土地感兴趣:“这是因为地上长了青苔,也叫生物结皮,这表明改造后的沙漠已经具备了土壤的特性,且性能良好。”易志坚解释道。

乌兰布和沙漠基地里的向日葵根系。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摄
总之,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片荒草地意味着什么。经过“沙变土”的力学改造后,2017年,易志坚团队在这片土地里种上了十几种耐旱的“野草”,比如沙打旺、柠条、梭梭、沙鞭草等等。第一年浇水,从第二年开始则完全让它们自然生长。8年过去了,易志坚没想到,这些野草在年均降雨量只有100毫米的地方越长越旺,将沙漠变成了绿洲。这似乎也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对照田,这块绿洲周围全是未经改造的沙漠,绿洲中的种子也会随风飘落到沙漠中,但是同样的降水、光照等自然条件下,沙漠依然寸草不生。
虽然这块“绿洲”每年也会有很多植被死掉,但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,似乎象征了技术应用的广阔前景。因此,这片最不起眼却又最神奇的地方,也是易志坚最得意的地方:一次改造,永续生长。或许这片神奇的绿洲,会将这片绿色和经验继续扩大、蔓延、生长,随之传播的,还有易志坚团队始终坚持的理念:不是一鸣惊人和吸引眼球,让自然保持自然,才是最终的目标。
作者: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